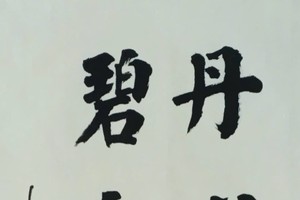我趕緊喊他起來,把兩條地巾疊在一起,鋪在地面上,示意他繼續工作。看著白色的地巾,他說這可不行,大姐,跪地上已經習慣了。我笑說地巾本來就是鋪 在地上的,弄髒了洗乾淨就是。他憨厚地笑著謝過,跪下去的時候,使勁拍打著褲子上的灰土。
他趴在那裏,很費勁地折騰了半天,跟我說是電路出了故障,這種情況一般都是拿回總部處理。但是他又說自己可以試一把,如果修不好不要投訴他就好。我說誰都不容易,怎麼可能投訴。聽了我的話,他的眉頭瞬間皺縮,給我講起了自己曾經的遭遇。那也是一個大姐,年齡跟你差不多,他說。那一次,也是電路出了故障,他試了一把,雖然很複雜,但還是修好了。收維修費的時候,那個大姐嫌收多了,開始挑毛病,說地面弄髒了,說他態度不好。無論大姐怎麼說,他也只能堅持公司的收費規定。他還沒有回到公司,那個大姐就投訴了他。公司領導開會狠狠地批評了他一頓不說,還扣了他工資。
看著他委屈的表情,我一邊開解他,一邊遞給他一大杯熱茶。他慌慌地推辭,說公司規定不允許。我說現在我是你大姐,不是你的顧客。他很憨厚地笑,接過茶杯咕咕咚咚地喝了,半跪在地上開始修電路板。電路板上燒壞了一根線,他用刀子仔細地刨開一條縫,埋進一根新銅絲,焊接牢固,開機試了試,挺好。他放心地填充了防水絕緣密封膠,安裝好洗衣機,我再次開機,一切正常。收費的時候,他只收了拆機費,他說電路板上只用了一根一寸長的細銅絲,不算什麼成本。他走的時候,我站在門口,看著他一級一級地走下樓梯,拐了彎不見了。只有歡快的腳步聲,在樓道裏有節奏地響著。我輕輕地帶上門,又想起了父親說的那些話。
那一次,是父親廚房裏的燃氣報警器壞了,我預約了燃氣公司的工人更換。計算好了工人到來的時間,父親提前泡了一壺熱茶。
操著一口浙江普通話的小夥子在廚房裏忙活,父親一邊看他幹活一邊跟他聊天。一會兒給人家搬凳子,一會兒給人家倒茶。父親端給小夥子的茶,都是大杯子,用手在外壁試了溫度,不涼不熱剛好入口。有些靦腆的小夥子,無法推拒父親的熱情,也確實渴了,接過杯子一飲而盡,連聲地說著謝謝。
更換閥門時,工具打滑,小夥子磕破了手指。父親慌慌地跑去臥室,找出碘酒和棉棒,仔細地給他消了毒,又纏了一條創口貼。小夥子離開我們家的時候,父親站在門口,直到人家拐出樓宇門看不見了,父親才輕輕地關上了門。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東跑西顛地幹活,誰都不容易啊。進了咱家的門,就是咱家的人,可不能慢待了人家。”
進了咱家的門,就是咱家的人。一杯37°C的熱茶,溫暖了你的,我的,我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