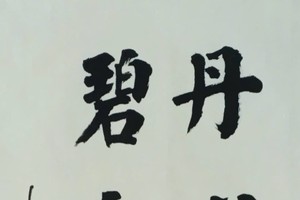爸不行了,這一次我一定要趕回去,見他最後一面。
說來慚愧,近20年了,我竟然沒有回家陪老爸老媽開開心心過過一天,每次總是像一個住店的過客,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似乎每一件事情都比回家重要,似乎每樣工作,都應該佔用回家的時間。一晃20年過去了,直到這次接到媽媽的電話,才突然覺得,日子真快,一向身體康健的父親,竟然要離世了,我真不孝!
父母是農民,是在土地上啃日子 的農民。年輕的時候,他頭髮咬斷七節,一家供出了3個大學生。現在本是跟著我們享清福的時候,可他卻不願意跟著我們,執意呆在家裏,啃他的一畝三分地。
記得他唯一一次進城已經是10年前的事了。那年,我特地給他安排了酒店,希望他舒舒服服多住幾天,誰知才3天,他就死活要回家。怎麼都沒留住。直到後來有一次他喝醉了我才知道,他要走的原因是,我沒有讓他進家門。
經過一夜的奔波,我終於到家了。然而,一切都已經晚了,父親已然離世。送喪的人倒是不少,來了一波又一波,門前靈棚高搭,挽聯低垂,鼓號樂隊滴滴答答,隆重而熱鬧,除帷幔是白色的以外,這情景,和小時候見過的婚嫁喜事沒什麼區別。
喪事的外表看起來很熱鬧,但屋子裏卻很冷清。父親躺在地上,穿一套藏青色中山裝,黃紙蓋臉,頭前點著一盞長明燈。除了母親和兩個姐姐守在一旁外,其他人都是自顧自地嬉笑打鬧,並無一點悲傷的情緒。
我走到父親身旁,一膝跪下。立刻,一個悲蒼的聲音從我的身邊響起:“爹啊!兒回來看你來了……”
我納悶地瞟了一眼。這人我並不認識,她不是我們家的親戚,幹嘛要在這兒嚎喪?我無暇多想,很快被她的哭聲所感染,不禁悲從中來,忘情地抓住父親的手,哀哀慟哭起來。父親的手冰涼僵硬,像樹皮一樣,乾枯粗糙,兩個指頭上還纏著灰白的膠布,也許他在倒下的那一刻,也沒有放下手中的活計。
良久,我總算止住了哭聲,擦乾眼淚。姐姐碰碰我,附在我耳邊悄悄說:“你還愣著幹啥呀?這些人是三哥請來哭喪的,人家已經陪你嚎了半天沒了,你怎麼還不給錢啊!”
哦!我明白了,難怪這人不認得,原來是三哥請來的“孝子”。我趕緊掏出幾張鈔票遞了過去。然後起身,去看坐在太師椅裏的母親。母親老了,滿是皺褶的臉上冷漠而悲涼。見我近身,她執著我的手,嘴唇動了動,又恢復了木然的神態。
時近正午,一個執事模樣的人走進來,對母親說道:“老太太,時辰已到,怎麼辦?老四還沒有回來!”
“不等了!活著都不看,死了還看啥!起靈,出殯!”執事應聲而去。
料理完父親的喪事,我們都鬆了一口氣。三哥真不愧為當官的,喪事辦得體面而隆重,給我們兄弟臉上增色不少。可是,父親去世了,母親還在,任務還沒有完成。她未來的生活,也成了我們幾兄弟頭疼的事。
雖然最好的辦法是有一個人能把母親接到自己身邊,好生侍奉。可我們這些弟兄,都各有各難處,都騰不出時間和精力來照顧老娘。大家商量來商量去,最後決定,還是出錢,將老娘送到敬老院。
可當我們把這個方案告知母親的時候,她默默地搖搖頭,拒絕了我們的“孝心”。然後把我們喊進屋,搬出一隻木箱,指著裏面一捆捆花花綠綠的鈔票說:“這是你們這幾年給我和你爸的生活費!你們自己拿回去吧!以後,你們也不需要管我。”說完,她搬開上面的鈔票,抖抖索索在箱底摸了半天,摸出一個手絹包成的包包,一層一層打開,拿出兩張老舊的存票。“你們算一算,你爸的喪事花了多少錢。你們把這錢拿去付帳吧。這些錢,加上鄉親們的喪禮錢,應該夠了!我的日子也不勞你們費心了。能照顧自己,你們都忙, 都有事業,不要因為我一個老婆子耽誤了你們!”
聽完母親的話,我們幾個兒子面面相覷。不知道老娘為什麼又犯起了倔?二哥拍了拍箱子裏的錢問道:“媽,你到底要什麼啊!”
“我要什麼你們能不知道?”母親反問了一句,袖著手,低著頭,匆匆出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