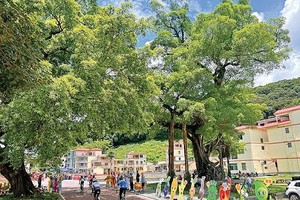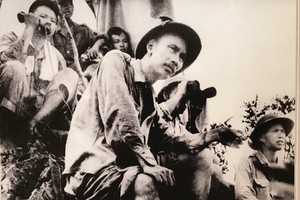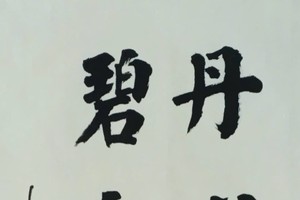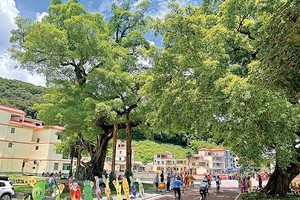有些人認為,文章能給越來越多的人欣賞,才是正道。他們常拿白居易說的“老嫗能解”來作根據,要求文章淺白易懂,做到老少皆宜。其實,白居易的詩作都能老嫗能解嗎?不,他大部分詩作與唐代文人詩無別,他這話主要是為諷喻詩與新樂府運動來立旗而已。可是他最著名的傳世作,恰恰不是這大白話的現實主義詩作,而是語言一點也不淺白的長恨歌與琵琶行。
淺白利於傳播不錯,可文章越淺韻味就越不足,只合一時閱讀,經不起讀後 的回味與時間的考驗,最終也難以隔世傳詠。
除了文字上的,還有立意上的深淺。這就是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的區別處。現代文學基本都是白話文,已無古詩文那麼艱澀難懂,現代讀者面對的,多是文章主旨與涵義的解讀。
通俗文學多以表像的情趣與情節的曲折為勝,立意淺薄又不離常俗,描述手法不求新意,因為迎合大眾口味,流傳得更廣。嚴肅文學以思想的深刻為主,故事性頗弱,敘述說法獨特,多把主旨隱藏在文字裏,意會者當會作深思考,不解其意者就味同嚼蠟。歷來的讀者都是小眾。
難道就不能雅俗共賞,像4大名著,情節與思想並重?雅俗共賞當然好,但又有多人能寫?這些名作多是長篇,有足夠的篇幅可讓故事性與思想性共存。其實說是共賞,就是各取所需,通俗讀者讀紅樓夢喜看木石戀,社會學家細看封建制度,政治家愛看政權鬥爭,文化學者就深讀其哲學思想。並不是所有讀者都能把全書內容讀透,真正的雅俗共賞本來就沒有。
嚴肅文學因為著重思想性,有著把情節淡化的傾向。而為了把讀者的感悟性提升,作者就採用了許多不常規的寫法。文學發展了好幾千年,好多題材都讓人寫爛了,用平常寫法就會令讀者產生審美疲勞。許多晦澀曲折的寫法,一方面提高了閱讀的難度,一方面更能獲得資深讀者的共鳴。
在各種藝術領域,都有俗與雅相對的現象,流行音樂與古典音樂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我們不能讓所有愛好流行音樂者能去欣賞古典音樂,可更不能否認古典音樂的級別更高。
所以,文學讀者應是廣泛大眾,可是沒有一種文學能同時迎合各種階層的讀者,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都有自己的讀者。在嚴肅文學範圍內,更應該能包容與推動多種嶄新寫法,別因為現在不懂就急於否定。時代在前進,以前難以接受的文學寫法現在已成常規,現在我們認為的艱澀,在不斷學習中,也將成銘心的閱讀經歷。
文學為誰而寫?一位前衛大作家說,他不需大眾讀者,世上只要有一個讀者能讀懂他,他就滿足了。曲高和寡,越高層的藝術欣賞者就越少,每一個先行者,就要有面對寂寞的勇氣,而作為讀者,我們應該為這些開荒者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