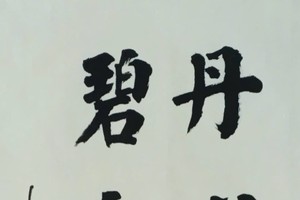那年,我高考失利,整夜未眠。父親看我臉色不好,問我是不是哪裡不舒服。我低頭說沒有。父親欲言又止,順手從兜裡摸出皺巴巴的煙盒,從中撿一枝相對筆直的夾在黝黑的食指和中指之間,劃柴點燃,愁煙彌漫。長時間的勞作,他的手爬滿了裂紋,我靜靜的看著父親的手。月光很亮,家中的燈也開著,我和父親坐在院裡,兩下無言。周圍嘰嘰呀呀的蟲鳴充斥耳膜,遠處的雞鳴在提醒我們夜深露重,該休息了。終於,父親手中紅彤彤的煙頭丟掉了,輕輕的落在地上,父親用腳踩了踩,煙頭依舊留有紅紅的星點。父親起身說,想複讀就複讀吧,無論你讀到哪,我都供。轉身進了屋裡。
我獨坐在院裡,月光很亮,把我的心都照得透明了。屋內昏暗的燈火透過窗戶落在我身上,我低眼看燈光遇物撒下的影子,眼淚落在影子上,毫無聲息。月光與燈光交織在一起,桌子與我有兩重暗影,像兩個有心事的少年互訴衷腸。我仰頭看月,依舊,我低頭看燈,依舊。
最終,我沒有複讀,進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學校。學校離家很遠,來回路程極其不便,每次去回都是坐夜車凌晨歸家。慶倖的是,天上有月亮做的燈等我,地上有父親在家為我點著一盞燈。每每回家,父親便半夜騎車去車站接我,寒冬酷暑依舊。每當如此,我都後悔去了一個偏遠的學校,以致父親在我回家時睡不安穩。父親把拿來的棉大衣裹在我身上,說晚上寒風冷。我坐在父親背後感受棉大衣的溫暖,父親在我前面,像我生命裡永不熄滅的光。
我坐在父親身後,他的背已不似當年堅挺,略顯佝僂的背被歲月侵蝕得只剩骨架。冬夜的燈光很寒很冷,月亮與我們為伴。那個年代,只有市區有燈,快到家的時候,一片漆黑。父親的車燈很暗,路亦顛簸,我緊張的坐在後面,抓緊了父親的衣服。父親自言自語又像是對我說,這條路我閉著眼睛都能到家。回家,是父親一生的責任。
伴隨叮叮噹當的車響,我隱約看到門口的微光。黑夜,那盞昏暗弱小的燈是那麼的明亮,刺透黑暗,指向光明。母親聽到聲響,起來開門,父親幫我準備好熱水,等我收拾好了,他再泡泡凍僵的手腳。我打擾過很多黑夜,愧疚使我無言。但即使凌晨3時,也有屬於我的燈為我亮著。那樣的夜晚,延續到今天。每有夜歸的我,都會有一盞叫父親的燈亮著等我。
很多年來,我忘卻了許多喜悅或悲傷故事,忘了很多人與物,卻始終沒有忘記那些夜晚的燈與月。父親是一盞燈,把自己的光都給了我。我走過沒有月的黑夜,也走過沒有燈的黎明,但我心裡總有一束光伴我前行。經年此去歸來,月與燈依舊。
今昔歸家,我在院裡抬頭攬月,燈火闌珊,父親依舊如往,只是斑鬢添霜。我在月與燈的暗影裡,歲如逝水,未走未遠。月與燈依舊,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