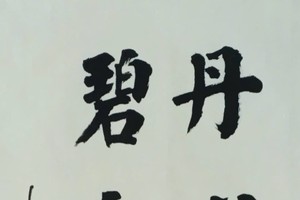晨光里的游人们提着竹篮,踩着青石台阶拾级而上。有穿浅绿旗袍的姑娘在花影里旋身,裙裾扫落几片花瓣,便惊动了伏在花蕊里饮露的蜜蜂。枝头新抽的嫩叶还蜷着身子,倒像是羞于与灼灼其华的花朵争辉,只肯在风过时轻轻晃动碧玉铃铛。山道旁的老茶寮支起竹棚,滚水冲开明前茶的刹那,白雾与桃香便纠缠着往云端去了。
我在半山腰遇见作画的老者。他支着桐木画架,笔尖悬在宣纸上方半寸,目光却久久停驻在枝桠交错的间隙。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几朵桃花正被山风托举着飘落,像是天空不小心遗落的胭脂扣,斜斜坠入下方深潭。潭水立刻漾开层层疊疊的粉色涟漪,惊得几尾青鱼倏然摆尾,搅碎了倒映的云影。
“画不得啊,”老人忽然喃喃自语,“这花骨朵里的灵气,比砚台里的墨色还浓三分。”说罢竟搁了笔,索性仰躺在青石上,任凭飘落的花瓣缀满灰白鬓角。他的呢喃被山风卷着掠过花枝,惊起几只躲在树冠里的山雀,扑棱棱抖落一阵花雨。
转过山坳,忽见两个孩童举着竹竿奔跑,竿头繫着褪色的风筝。断线的纸鸢正卡在桃树枝桠间,残破的蝴蝶翅膀上还粘着去年的槐花。穿碎花袄的小丫头踮脚去拿,却把枝头的花苞碰得簌簌摇晃,粉白的花瓣便落了她满肩。后边追来的少年笑得跌坐在地,惊飞了草丛里饮水的蓝尾雀。
正午时分,游人渐渐往山脚聚去。野餐布在桃林间次第铺开,格子纹的、碎花的、靛青粗布的,倒像是给草地打了各色补丁。穿藏青布衫的老茶农担着木桶沿路叫卖,陶碗里的桃花蜜水盛着细碎日光,引得姑娘们鬓边的绢花都失了颜色。有穿月白长衫的书生坐在树根上读书,忽被飘落书页的花瓣迷了眼,再抬头时,正撞见枝头麻雀歪头打量他的呆样。
风起时,整座山谷都成了飘摇的绸缎。花瓣纷扬如三月雪,落在游人的伞面上、竹篮里、发梢间。穿藕荷色衫子的妇人蹲在溪边浣帕子,忽见水面漂来几片残红,便伸手去捞,却搅乱了倒映的蓝天,指缝里漏下的水珠都染着淡淡胭脂色。
暮色初临时分,我登上观云亭。西斜的日头给每片花瓣都镀了金边,远望如万千烛火在山间明灭。晚归的黄牛从桃林穿过,牛铃叮当惊起满地栖息的粉蝶。山脚升起袅袅炊烟,与尚未散尽的花雾缠作青灰色的纱帐,将整片桃林笼进温柔的暮色里。
忽听得山下传来清越的陶笛声。循声望去,见玲珑少女独坐溪畔巨石,十指在陶笛孔洞间起落如蝶。笛声裹着花瓣顺流而下,穿过石桥洞,绕过捣衣台,最终消逝在暮色苍茫处。此刻山风骤歇,千万朵桃花忽然静默,彷彿都在侧耳倾听这支烂漫的春之谣。
当最后一缕夕照掠过山脊,桃林深处亮起点点灯火。护林人的小木屋窗棂上,贴着新剪的桃花窗花,在灯光里投出朦胧的影。夜露悄悄爬上花瓣时,我听见满山花树在黑暗里舒展枝条的声响,像是无数细小的铃铛在风中私语——明日,又该有新的花朵睁开睡眼,把这漫山春色再添三分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