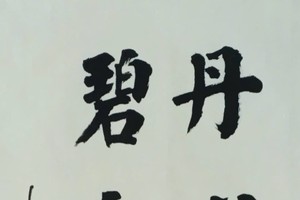那時,我沒有皮棉帽,沒有保暖內衣,沒有厚手套,山谷裏呼哨的風刺剮我的耳朵、手掌、腳背。我的耳朵厚實了,臉蛋青紫了,手腳背成饅頭了,指頭成胡蘿蔔了。凍瘡如期而至。皮膚下有硬塊鼓起了包,奇癢如小蟲鑽進了骨頭,用手撓,用嘴咬,用腳蹭,包越大越亮,“啪”,裂開一個口子,流出膿血,掉著血痂,鑽心般地疼。這凍瘡彷彿在我身上紮下了根,年年冬天都發芽、 生長。
母親疼在心口,她不要我受傷痛,她要打敗凍瘡,剜去凍瘡的“根”。
家裏養兩隻“自留羊”。夏初,剪了羊毛,大部分賣了,換成了家裏的油、鹽、醬、醋和我的學費,母親留下一些。耕種歇息時,母親撚轉線陀紡線;深夜煤油燈下,母親給我編織毛襪、毛手套。但母親編織的這些“武裝”,卻未能抵擋住凍瘡對我的進攻。
聽說用牛糞敷,能治凍瘡。晚飯後,母親讓我做作業,她裹緊衣服出門了。暮色昏暗,厲風嘯叫,冰粒打面。“咯吱、咯吱”,母親踏著厚厚的積雪行走在山坡上,她弓身尋找牛糞。牛糞是地裏的肥料,撿牛糞能折算工分,山坡上的牛糞很少。母親走很長的路,才撿來兩三坨。母親哈著氣回來,額頭、眉毛結上了冰霜。母親把牛糞放在鐵爐上,“滋滋”,牛糞呻吟著冒出白汽,屋子裏充斥尿臊味。母親拿起濕熱的牛糞用手試試,摁到我手背、腳背、臉上的凍瘡處,溫乎乎的燙熱滲到骨頭裏,舒坦熨帖。每晚,母親給我敷半宿,但這個辦法收效甚微。
母親從村衛生所的赤腳醫生那兒討來一個土方。她把薑片、乾辣椒放到鍋中,“咕咚咚”熬水。水呈褐紅色,水放溫熱,母親讓我洗手、洗腳。我疼得呲牙裂嘴,母親鼓勵我:“長痛不如短痛,男子漢要忍住。”母親要“以毒攻毒”滅掉凍瘡,但這辦法太疼,我受不了。
母親又打聽到蘿蔔渣效果好,她把蘿蔔切成碎沫,放到鍋裏煮,打撈出蘿蔔渣,包在紗布裏,熱敷到凍瘡處;母親找來獨頭紫皮大蒜,搗爛成蒜泥,用醋調和,塗抹到凍 瘡處……
母親用盡了辦法,也沒剜去紮根在我身上的凍瘡。但 母親與凍瘡曠日持久的戰鬥,卻永遠烙進我的記憶。以致現在回想起來,凍瘡的痛感早就消逝,但母親的溫暖卻長留 心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