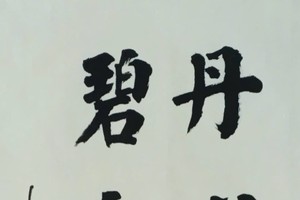柵欄門被推開了,雲兒蹦蹦跳跳地跑進來,向我展示她烏黑髮辮上的梔子花。雲兒是我的玩伴,我們兩家相鄰,她長我兩歲,生得白淨秀氣,在一群皮膚黝黑的小夥伴中格外亮眼,如路邊的杜鵑,沒有人呵護也能開出美麗的花。
村前有條府河蜿蜒而過,河堤坡上野草叢生,野花散佈。沿河坡邊有片林子,樹木蔥蘢,遮天蔽日。放學後,雲兒喜歡帶我跑到河邊採野花、摘桑葚、拔毛根,跑上跑下像兩隻快樂的精靈。
一天,雲兒突發重病,持續昏迷,醒來後卻不正常了,10歲的雲兒得了精神病,當我看到她時,張牙舞爪的咿咿呀呀叫,身子搖搖晃晃,嘴角歪斜流著口水。我頓時蒙了。
母親說雲兒連續高燒,燒壞了腦袋。
我童年的小夥伴,從此在人間搖搖晃晃。
後來,我轉到城裡上學,回家當然也不會和雲 兒去河邊瘋跑了。隨著日月輪換,我和雲兒越來越 陌生了。
17歲那年,我又見到雲兒,她手裡拽一把野花,搖搖晃晃地指著河堤,咿呀地地說著什麼。我驚訝地發現,雲兒亂蓬蓬的頭髮上,戴著一朵黃色的野菊花。
母親說,雲兒戀愛了。自從戀愛後,雲兒就愛美了,標誌就是頭上不停的戴花。
對方是鄰村的青年,聾啞家貧。殘疾配殘疾,貧窮對貧窮這樣的組合,在我的家鄉很常見。一個輕微智障,一個聽不到世界的聲響。這樣門當戶對的組合,是正常人的談資,予他們未嘗不是苦難人生中開出的嫵媚花朵。
河堤上野花開不盡,雲兒的花兒戴不完。聾啞青年經常牽著搖搖晃晃的雲兒,去河邊採野花。他把喜歡的花兒摘下,插在雲兒的髮間。
春天,雲兒的頭上,有黃色的蒲公英、紅色的紫雲英,還有桃花、杜鵑、野薔薇……整個春天,在雲兒的髮間和聾啞青年的手指上,次第開放。
這樣的兩個家庭,這樣的兩個青年。縱使不是天造,在地上也很般配。兩家將婚事商定在五月,生活似乎見到了亮光。
事情出在春末。他們在河邊採花,聾啞青年追趕一朵被風吹跑的花兒,不小心滑進了河裡……殘疾人也有愛情,可是,再溫情的河水也會淹死人。他們靈光一現的愛情葬送在河水裡。
那年初夏,19歲的雲兒,戴著一朵金黃色的油菜花,咿呀地指向河邊,含糊不清地對我說,河邊曾有一個給她戴花的男子。
我問雲兒,為啥喜歡戴花?雲兒輕撫花朵,張嘴帶動面部有些猙獰地說,美!
夏日的午後,驟雨初歇。府河岸邊綠柳如蔭, 芳草淒淒。我和雲兒再次來到河邊,她邁著慣常搖搖晃晃的步伐,彎腰從路邊扯下一朵葵花,對著水面 想戴上,向日葵太大,不方便戴在頭上,她便將向 日葵抱在懷裡。河水裡,映照出一個女子樸素純真 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