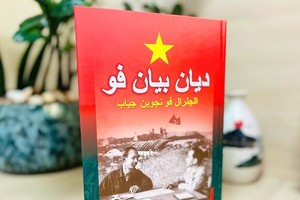人生在世,离不开衣、食、住、行。这四字看似平凡,却支撑着每一个清晨日暮、每一段悲喜人生。其中的衣,不只是蔽体御寒的布料。它是身份的象征,是自尊的外壳,也是人与人之间无声的语言。对西堤的华人来说,“衣”还是一种文化,是一段历史的剪影。
西堤华人服装的进展
据1949年出版的《西堤华侨社会总览》中谈及“华人服装的进展”写道:20年(指上世纪30年代)前刚从唐山移居西堤的华人穿着,简朴得几乎可以用“素净”来形容。街上常见的,是唐装与长裤,脚下一双皮拖鞋便可应对日常与宴席。即使是商界颇具声望的老板,也只是穿着一身白色斜布立领的中式西装,整洁但毫不铺张。那时的风气,是克己与节制,是一种对生活本质的静默敬意。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物换星移,人们看待彼此的眼光早已从内在延伸至外在,讲究起“先敬罗衣后敬人”的礼数。于是,华人的服装也悄然改变了:立领的中式西装逐渐被衬衫与长裤取代,更多人穿起了英伦或法式绅士装,仿若要用一件西服向文明世界递交名片。这一身打扮在许多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尤其是华人的主流社团盛大活动中常能见到。
西堤的天气常年如夏,白色成了当年华人最常穿的衣服颜色。年轻学生们穿着白衬衫搭配黄短裤,女孩子则是白衫配黑裙,一派清新明亮。一般人则因职业与习惯,有的穿长裤,有的着短裤,风格各异。洋行里的职员与老牌商家则讲究些,常见美式西装或法国薄呢,一针一线皆为品味所致。而当年的基层员工与劳工,多穿丝质内衣或短袖背心,既凉爽又实用。那时候物价日渐高昂,生活压力重重,他们每日辛劳,所得仅够果腹,要在衣着上再添支出,无异于雪上加霜。但这样的时代,谁又真的能不在意穿着?
至于那些富家子弟,打扮便显得格外出格。他们身上的衬衫五彩斑斓,红绿交错,有的还绣着花草与人物图样,在街头巷尾招摇而行,仿佛每一件衣服都是一场特立独行的表演。他们称之为“原子时代的新装”,却常让人摇头叹息,不知是风格还是浮夸。而太太小姐们的服饰,更是日新月异。裙子忽长忽短,款式变换不停,追求身形的线条与柔美,对布料的讲究与手工的昂贵从不厌烦,似乎只要够时髦,就值得一切代价。她们穿在身上的,已不只是衣服,而是一种态度,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表演。
上述对西堤华人近百年的时装描述,在现代人的眼光中也许没什么独特,但它却反映了一个族群的一个时代的生活变迁。这到底是时代进步的象征,还是一场虚荣的幻影?在华服与喧嚣背后,谁又还记得那份朴素中的从容与安静?
养妻活儿话裁缝
于1950年出生的梁建刚是第二代华人,他的父亲梁锦14岁从广东开平观塘乡跟随乡里梁南裁缝师下南洋来到堤岸,最初是在梁南裁缝店里当学徒,学成后自立门户,开了新华裁缝店,与妻子共同经营。
他们最初是在原第五郡阮廌街的一条巷子里租房开店,后来迁到原第十一郡白铁街市“织箩侵”去。那时候子女成群,为了养妻活儿,梁锦夫妇日以继夜地为客户缝衣服。梁建刚忆述,在“织箩侵”生活的那段日子是最艰难,他们兄弟姐妹穿的衣服都是父母缝的。有时候深夜起来时还看到父母在一盏小灯泡下缝衣,“咔嗒咔嗒”的衣车(缝纫机)声犹如母亲的催眠曲伴随着他们度过每一个夜晚,如今事隔大半个世纪,偶尔在睡梦中还听到熟悉的“咔嗒咔嗒”声。他们兄弟姊妹七人是靠父母的裁缝店养大。梁建刚也说,他们前后换了好几个住所,但每次都把裁床和剪刀带上,这是父母的生活工具,所以对赖以维生的工具一直不离不弃。父母去世后,他们兄弟姊妹虽然没有谁继承家业,但裁床和两把剪刀成了梁建刚的“家传之宝”,无论迁家到哪里,他都把它们带上,尽管后来裁床的四根木脚被白蚁蛀蚀,但他把损坏的部分锯掉以把裁床保存下来,有段时间他还将裁床当作午休的木床,躺在光亮的木板上有种凉快之感,非常舒服。
这张拥有80多年历史的木板裁床和父母留下的两把剪刀被梁建刚视若珍宝,这也是父母把他们兄弟姊妹养大的谋生工具,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纪念价值。然而,最近得悉笔者在收集西堤华人老物件,梁建刚却割爱了,他主动联系我们,希望为西堤华人文化陈列室的建立添砖加瓦。
翻阅1949年出版的《西堤年鉴》,在中西服装公会的介绍中,笔者意外发现了梁锦的师傅梁南是当时的公会成员之一。
中西服装公会于1946年7月2日成立,当时的会址设在堤岸津卫街十七号,为一劳资合作之社团。其组织采理监事制,由理事15名组织理事会,监事5名组织监事会。梁南为15名理事其中之一,其他理事为侯和,梁明,梁大,陈连,袁俊华,程作,梁美贤,冯来,骆文,陈华国,黄强、叶应贯,吴奕强,黄森等,监事为梁波,张广,陈权,谭根,董嘉兴等5名,全体会员共有200多名。活动经费主要由各商号月捐及会员月捐。从此可见,西堤华人裁缝业也有悠久的历史,是华人时装进步的推手。
岁月流转,时尚更迭,但我们今天所穿之衣,所走之路,仍离不开那份脚踏实地、默默耕耘的精神。愿这张老裁床与两把剪刀,不仅存放于西堤华人文化陈列室的一隅,更长存于我们对老西堤、对华人历史的深情凝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