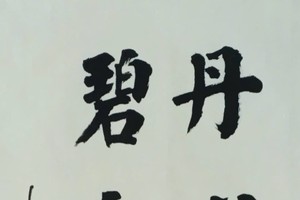她說:婆婆癱瘓5年,都說久病床前無孝子,我們對她的照顧,兄弟姐妹多年輪流守護,真的身心交瘁,這一走心裏還總是有些不捨。姐姐開始輕聲抽泣。
是啊,一個癱瘓的老人,在生命最後的時刻卻走得很尊嚴,這麼多年孩子們盡了孝心,臥床多年,老人身體沒有褥瘡,乾乾淨淨,而姐姐對待老人無微不至的照顧,像對待一個嬰兒,餵飯,餵水,換紙尿褲,我想這就是反哺。
姐姐那頭沉默許久……
她還說:老太太走之前,眼睛睜睜閉閉,喘著粗氣。“鑫鑫回去了嗎?”我焦慮的打斷姐姐的話不停的問。鑫鑫是姐姐唯一的兒子,也是姐姐婆家的長孫。”在回家的路上,這裏很忙,客人都陸續來了。”姐姐還未說完匆忙掛了電話。我想,姐姐的婆婆一定是在等待她遠方回家的孩子……
撂下電話,我呆坐沙發許久,靜靜地,那碗孟婆湯還在悠悠飄著熱氣,似乎,空氣被沉重凝聚,再也沒有胃口喝下。
窗外,此刻天還未盡黑,狗狗坐在對面愣愣地看著我,對我的鎮靜有著不解甚至有些恐懼,不停的邊叫邊退,邊退邊叫,焦急亂蹦,狂躁不安,它貌似懂了我此時的心情。
猛然懷想起一個人,姥姥。一個失明的小腳老婆婆,每天晚上會在微弱的煤油燈下,看著她洗腳時脫掉小腳的裹布,那一刻,我總會躲到她的紡線機旁,遠遠的看著她,裹布繞腳很多圈,很長,很臭,解開的那一刻看到了姥姥那變形的雙腳,卻很白皙……
而姥姥,雖雙目失明,她總是咧著嘴笑我的躲避。猛然,也似乎讓我感受平生最不願回想,回想親人的離去。那種痛,一直隱藏在內心深處。姐姐是個堅強的人,她的語言哽咽帶著悲傷,總是停頓許久,想必她此刻想到久遠的兒時。
我壓制自己,卻沒有更多語言。回到幼年時光,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奔跑在田埂間的夥伴,快樂無比,一起趕鴨,一起石頭剪刀布,一起紮堆吃黃瓜,比比誰家的黃瓜大而粗,還有一起提著籮筐跟在姐姐後面偷鄰村的豌豆,筐子很大,用胳膊挽起不時的磕碰著自己的雙腿……回家,姥姥總是摸摸我的臉蛋摟在懷裏,是憐愛還有責備。這是今生中一個人對我寵愛的唯一方式,也是僅有的方式!
掩面,狗狗仍不停的叫喊。每次回到家鄉,會去看望姐姐的婆婆,與她短暫的交流,總會問:大娘,您還認識我嗎?”她已經認不得人了”姐姐搖搖手輕輕的說大娘的聲音微弱,只能將耳朵貼近她的嘴邊“你是鑫鑫小姨。”大娘的聲音很小,我卻聽得一清二楚。“哇”我驚訝的叫出聲來。姐姐說:她時而清醒時而糊塗,從不吵鬧……
我的內心好似五味雜陳在翻滾,大娘的意識還是清醒,那一刻,我站立很久,看著她,只希望,只希望她能在世間多活些日子。
如今每次想起,我們活在這個塵世,最終都會與生命告別,只是方式不同……
一位這樣的老人,在剩下最後的日子時,癱瘓多年,一身骨瘦如柴,她曾經的那股子志氣,除了離世,一切都帶走了。
我相信,她亦不再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