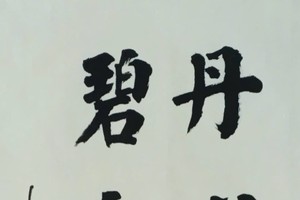憋悶了一個冬天的西南風,毫不猶豫地打翻了大自然的調色板。陽光普照下的故鄉田野,嫩綠、深綠、墨綠,嫩黃、深黃、金黃,淺紅、粉紅、深紅,七彩雲霞似的,明晃晃地耀眼。興奮的大人孩子們,腳步聲紛亂,撲撲噠噠。笨重的馬車牛車,轍印縱橫,吱吱扭扭。人和牛馬一起從村莊裏晃悠出來,走過村南的小橋,去望不到邊的雲霞裏撒歡。
橋下的溪水澄碧,嘩嘩啦啦地流淌。水岸邊一片片青蔥的蘆葦,翠綠的茅草,金黃的小野花,在甜絲絲的風裏,窸窸窣窣地飄搖。圓滾滾的鵪鶉隱在草叢裏,哇哇歸歸地歡叫。伶俐的小燕子,“嗖嗖”地掠過水墨畫似的麥田。一壟壟返青最早的麥苗,正在嗶嗶啵啵地拔節。一匹匹高頭大馬,一頭頭好脾氣的黃牛,拉著錚亮的犁鏵,在油汪汪的土地上來來回回。黃河浪似的泥花,呼呼啦啦地卷起來,呼呼啦啦地落下去。肥胖的蠐螬,驚慌失措。白色的茅草根,嗤嗤地斷裂。
秋天遺留的玉米根,累累墜墜地被掀了出來。看著滿地的玉米根,我們不找茅針,也不攆蝴蝶了,一個個提著小鎬頭,衝進煊軟的土地裏,撿起沾滿了泥土的玉米根,用足了力氣往鎬頭鎬把上磕。隨著哢哢哢的聲音重疊,濕漉漉的泥土四處迸濺,嘻嘻哈哈的笑聲也四處迸濺。撿得累了,隨手挑一些粗壯的茅草根,用手捋捋,用褲子蹭蹭,咯咯吱吱,嚼得滿嘴生津。泥土香,草根香,野花香,混合在一起,迷醉了人,也迷醉了風。
磕掉了泥土的玉米根,支支棱棱,三五個就裝滿了草筐。一直堆到筐把上去了,我們才會深一腳淺一腳地,從地裏掙扎出來,一筐筐地倒在長滿野草的溝坎邊晾曬。晾曬乾了的玉米根,運回家裏,堆在雞窩旁邊。做飯的時候,母親拔幾棵菠菜,掰幾束香椿芽,點著一把軟草引燃玉米根,鍋裏劈劈啪啪地響,玉米根劈劈啪啪地爆,綠白分明的菠菜粥咕咕嘟嘟地冒泡。
菠菜吃完了,還有滿樹的榆錢。我們把長長的竹竿頭劈開,橫著夾上一根小樹棍,站在榆樹下,仰著頭一起尋找。這根多,夾這根,那根長,夾那根,七嘴八舌,吵架的麻雀一般,嘰嘰喳喳。長得最高的孩子,舉著竹竿,對準了榆錢最密集最鮮嫩的樹枝,夾住了,哢嚓折斷一枝,哢嚓折斷一枝。性急的男孩子,蹭蹭蹭三兩下就竄到了樹上,塞了滿嘴的榆錢,心滿意足,哈哈大笑。
菠菜收了種子,榆錢搖了響鈴,母親用鐵鍬翻松院子裏的菜地,刨了一個一個的小坑,點種豆角、玉米、大黃豆。一粒一粒飽滿的種子撒在坑裏,金黃的陽光也灑在坑裏。我在院子裏又蹦又跳,大聲地喊著種太陽嘍,種太陽嘍。母親停下手裏的活計,開心地看著我笑。放了學的哥哥,遞給我幾支柔軟的柳笛。我們站在陽光明媚的院子裏,把碧綠的柳笛一起吹響。一陣陣清脆悅耳的聲音,高高,低低,樸素,悠長。如一泓載滿了鳥語花香的清泉,在春天的田野裏,叮叮咚咚地奔湧,不知疲倦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