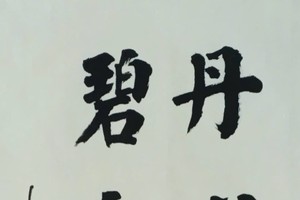山影沉沉的黑夜中,魚兒劃過的水聲和她的笑聲多麼輕靈,我常常想起月光下的水粼中和她坐在溪邊,她帶著一包花生一壺水,和一堆氾濫的情懷,說著許多空幻的心事,映著月光的溪流,月越晚越空靈剔透,常常是等到溪水緩緩的漫過了大石,濕了裙角,才知道潮汐漸漲,夜更深了。我們便拿著手電筒,照著彎路,走回那片竹林。
她的家,在山腰竹林間那條掩隱的彎路上,她常拎著一根竹棍,打著草,領著我,走著崎嶇的山路,融入晨嵐暮色看煙雨陰晴,看小溪奔騰山巒間的各種變換。她的舊鞋底,把徑上的竹葉擦著沙沙做響,這土城的山郊一些奇特的花草,菌菇,蜘蛛,蛙蟲她都懂,她說:土城,能繞的就這山這澗,這山這澗聚集的便是這些山靈。
我總愛到小城找她,踩著高跟鞋隨她到市集溜達,被她慫恿著去澡堂洗個別開生面的熱水澡,去看一場二輪電影,摘摘果子,野菜,吃吃路邊的陽春麵,偶爾被側身而過的口哨聲吹的臉紅心跳的,晚上便到溪邊等待滿月或星空下的銀光流瀉,撈著湍湍流水裏的詩句,然後在露痕草香的竹榻中睡去。
她嫁了,又是老遠老遠的海邊,我們都向婚姻要了第一個願望,把所有的夢,日子奉獻給以為是大山的男人。記得,送她到車站時,她一身紅洋裝,拖著紅皮箱,好像是她那少女的一切,簡單到只裝進了一隻皮箱,就隨著剛闖入情懷的口哨聲遠去,開始了她的人生百味。這一身燦爛的紅,紅得有點土氣,紅得我幾乎記不得她的姣好身段,和那股山靈的仙氣。一團氣煙帶著那一團紅,和身邊那巨大的黑影,就在我潮濕的眼眶中消失。
命運還是贈了她一幅素雅的水墨山水,卻讓我鑽進了百匯叢林,她隨著他去了海邊的小鎮,我去了海的那一邊,從此土城歲月就畫上了句號。我羡慕她坐擁天地,她卻羡慕我繁花看盡,我們都在天涯海角風雨中洗禮著。
那年,正是秋金送爽,家門前滿地落秋,枝頭掛滿了金黃艷眼的楓,我飛越重洋去看她,她已是兩個孩子的媽,清麗的短髮紮成了一撮馬尾,海邊的秋,時而艷陽,時而清冷,一樣風刮著落葉,一串串的醃製的臘肉,香腸,掛滿了竹竿,她說:這風,正是晾臘味的好時節。
陪著她洗醬油樽,看著她整天在曬著一缸缸醬油的大院忙著,那密佈刺鼻的豆瓣味,濃得我受不了,她卻說聞慣了就香,原來,這時間沉澱下來的豆鼓味,每一個層次都是一種等待的成果,真不知道她怎的那麼俐落,堆得像山的玻璃樽,一個個的在她手裡晃當兩下,那髒水,就隨著漩渦傾瀉而出。而我,只能從體驗中,進入這個優雅,聰慧美麗的女人心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