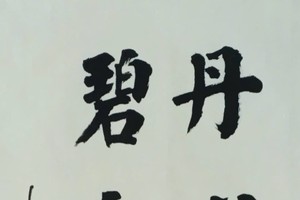那時土城的山林溪水間,我們編織很多的夢,許了很多的願,卻都沒有完成,有更多的是,我們的心思,都比以前沉了好多,卻又學不來雲淡風清面對世事,畢竟我們是那麼的年輕,對那燦爛或滄桑的未來還有無限的嚮往。
她還是一樣,討著我歡心,帶著我,到島上最西邊的海邊看浪花,海風很大,我們用勁踢著浪花,像是想踢走彼此之間被不同的生活框架擋住的隔閡,誰都不想壞了留在彼此心中的美好。她濃眉下一雙清澈的眼睛,多了一些化不開的漣漪,紮了馬尾的長髮,留下幾根在汗水中飄著貼著的髮絲。
那一夜,我和她依著床,窗外的街燈照著大半邊牆,晴朗的月亮在很高很遠的天際,我說,是小溪的月亮嗎?怎麼離得那麼遠?我賭氣地說:這月光,分明不是土城的那輪皎月。我說:還那麼任意媽?很想那個餿主意的你,很想那個山中!她什麼也不說,只是在晃動的牆影間,沉默著,睫毛下的那潭湖水卻隱約的閃著光。我們的臉,被窗外的街燈,閃得一暗一亮的,靜靜的夜裡,我才領悟人生的聚散,豈能從心,我的心在一明一暗間百感交集。
她說:那裡竹影不再,彎徑已不見,小溪依舊緩緩,山色依舊巍巍,枕著小溪水上的石子,依然朝暮伴著青山流水,她問我:當年的心還在嗎?我也默然,當初,哪有永遠的當初?
後來,土城的山,土城的小溪,還有,海邊的曬穀場、醬料味,竟然真的都成了只是回憶裏一幅畫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