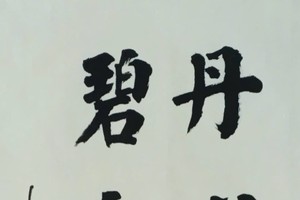老屋廊簷下,果真掛著個燕子窩!窗前一根生銹的晾衣繩上,歇著一對灰黑的燕子。牠們相互梳理著羽毛,親密地呢喃著。那聲音甜糯、輕柔,像一把細毛刷子,拂拭出我內心積壓已久的前塵往事。
那年春天的一個清晨,我被一陣唧唧聲吵醒,我蹬了一腳還在酣睡的母親:“媽,啥鳥在叫?”母親豎起耳朵,隨即翻身下床,打開大門,接著傳來驚喜的呼喚:“燕子!燕子呃!燕子來咱家做窩了!”
我一個鯉魚打挺,歡蹦起來。哇,真有兩隻灰黑的燕子,在門前的木槿籬笆上啁啾,而廊簷下的牆壁上,已經粘了許多泥巴和樹枝。父親也很高興:“太好了!咱家也有燕子了!”
在我們家鄉有個說法,燕子在誰家築巢,就會給誰家帶來福氣和財運。紅霞家年年都有燕子,她哥就成了村裡第一個大學生。我摸著母親隆起的肚子說:“媽,要是生個妹妹,就叫燕子吧!”母親白了我一眼:“呸呸,快改口說是弟弟,弟弟!”
我知道父母天天都在盼著生個弟弟,我不喜歡弟弟。灣子裡的幾個小弟弟,全都是鼻涕蟲!我絕不改口,目光追隨著那兩隻翩飛的燕子。只見牠們撲棱著翅膀,尖嘴上銜著細泥和雜草,又飛到咱家廊簷下了。
此後,牠們每天飛來飛去,不久,一個半圓形的燕子窩就做成了。春末,兩隻乳燕破殼而出,整天唧唧啾啾。如果老燕銜蟲歸來,牠倆就探出腦袋,伸出小嘴爭食。
那天午後,我坐在門檻上,沉醉在燕子的吳儂軟語裡,赤腳醫生義安姨在屋裡喊:“蓉兒,你媽給你生了個小弟弟!”我跑進去一看,父親正喜呵呵地包裹那個紅皮膚、皺巴巴的小東西。我撅起嘴巴:“怎麼不是妹妹?”義安姨說:“傻丫頭,是弟弟,你才是嬌嬌寶貝!”
弟弟越長越白胖,一逗就咯咯地笑,我越來越喜歡他了。母親抱著弟弟,跟人說話也高聲大氣起來。父親更像是撿了金元寶,整天眉開眼笑。那時候,四隻燕子在上面唧唧喳喳,四個人在下面嘻嘻哈哈,我們家呈現出從沒有過的歡樂與生機。
後來,我外出求學,寒窗苦讀。我並不知道每年春歸,燕子是否還來咱家築巢。直到父親在驚蟄的雷聲中猝然離世,我問母親:“媽,咱家的燕子呢?”母親木然地望著空空的廊簷:“年年都來,就今年沒有。”
10年後的初夏,正是雛燕啁啾的季節,母親也走了。我下意識地望了一眼屋簷,只有一隻破舊的老巢。看來燕子是通人性的,牠比我更早知道家裡的變故。此後,弟弟在鎮上安了家,我就再沒回過這個空巢。
我萬沒想到,在人去屋空多年後,還有燕子在替我守家。在年近半百後歸來,還有燕子在親人般把我迎接。站在銹蝕的鐵鎖面前,看著牠們那沒被時光改變的烏亮的羽毛,聽著牠們唧唧復唧唧的鄉音,我的淚一顆一顆掉下來。
燕子聲聲裡,相思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