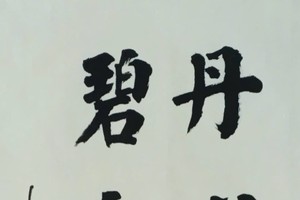街巷,偶爾雞鳴,偶爾狗吠,挑撥起一捧捧微醺時光。
春將盡,草長鶯飛,有一場花事又在趕來的路上,不幾日,街巷兩側這些抽枝生葉的老槐樹,便會一咕嘟一咕嘟冒出許多花,像甜膩的白衣女娃,嘟著嘴,肆意美麗著。
這個時候,如果親自在花樹下走一走,體會到的那種感覺是,一塊梵古畫布,被用熱烈原色塗抹著對生命的熱愛。二里多的街巷,兩側開滿了槐花,高大茂密,而之上又是需仰望才看到的漸次開了密密的花的枝條,早晨的陽光灑落在枝葉的空隙和它們的身上,光影鮮亮。或走或站或仰望,花和花骨朵和翠綠真實,讓人驚訝不已,如果目光和陽光牽手,會是一對新鮮的蝶,快樂起舞。
這街巷沒有荒涼過,一直渲染著它的生機,如果再挪把椅子在房檐下,萬朵陽光覆蓋,會讓我不由得下想到一個人的懷。
是媽媽
不停地做夢。夢裡,住著槐花,陣陣香氣繚繞,揮之不去。
只是重複一樣的場景。年輕的媽媽帶著我,舉著鐮刀,踮著腳尖去夠樹上的槐花。
白嘟囔囔,白嘟囔囔。滿世界的清香,有的,落在我仰起的小臉上……
槐花有很多吃法,可以做槐花丸子,炒槐花茶,槐花包子,槐花餅,尤其曬乾的清河魚蝦兌上新鮮的槐花,再擱上厚厚的豬油。饑餓一下子被填得很滿。
槐花不但可以食用,也是一味良藥,可以止血涼血,防止毛細管脆性過大,滲透性過衰引起的高血壓,糖尿病等。
童年的小船起航,剛剛駛出駛進五個年頭,媽媽病了,但住在老街巷的我,沒曾想過不讓媽媽吃上槐花。
每每這個季節,老街巷便五彩斑斕,多顏色的人從街頭或巷尾或雨後或黃昏迤邐出來,笑容婉轉,似乎比清河的魚要多,還有的挎著相機,眼睛跟著蜜蜂飛。
媽媽這樣告訴我,可以用竹竿綁上彎鐮,自己學著去捋花,花可以捋,但絕不能毀斷樹枝,槐樹是咱們老街巷的,保護好了,才可以讓更多的人年年有槐花吃。
聽了媽媽的話,我去捋槐花,但我坐在門口,讓彎鐮躺在腳邊,抬頭看著層層疊疊的樹頭,樹頭裡小小白色的花朵,一串一串的,白色葡萄似的倒掛枝椏上,幾個不認識阿姨從身邊走過,嘻嘻哈哈,顧盼裡,都是風情。當她們再經過我身邊時,每人手裡拎著袋子,一個胖乎乎阿姨走過去,又轉回來,問我:“小朋友,看你腳邊有鐮刀,是不是想捋槐花?”,我點點頭,沒說話。阿姨說:“我弄得多了,吃不了,勻給你一些吧!”我搖搖頭,沒說話。阿姨又說:“你住在這,這槐花是你們的,我們來弄你們槐花,本是不應該,這樣吧,咱一人一半,你若願意呢,我過年還來捋槐花,過年還來捋槐花,一直到你不讓我們來為止。”
這個胖阿姨是市里的,因為老街巷的槐花,因為我笑著答應了阿姨,她就成了老街巷裡每年流動的風景。
而我,一直像槐花一樣袒露在季節裡。枝枝杈杈,儘是您給的柔軟。
當然,槐花也落。槐花是一種內斂沉默的花,藏在茂密樹葉裡,沒見全開就落了,一地玉碎。落了的依然嫩黃翠綠,也是沒開盡的樣子,像欲說還休,像欲愛不能,像情至濃時愛人卻抽身而去。
又是槐花飄香時,我學 著媽媽,叫著上小學的兒子說:“今天,我們一起去捋 槐花。”
槐花香,槐花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