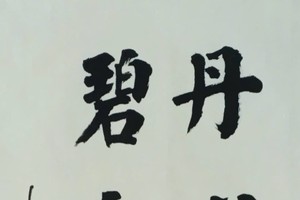男學木匠女學裁縫,這是當時我們農村孩子的共同命運。我的兩個堂姐都學的裁縫。我親眼見到她們給裁縫師傅的小孩端屎把尿,還受到大聲呵斥。我打心底不願學裁縫!可那時師範院校的錄取分數比本地一中高很多。我並沒有十足的把握能夠考上。
我要讀書!我要通過讀書改變命運!如果考不上師範,我就去讀高中,考大學!這是我當時唯一的心聲。可家底寒薄,父親身患重疾,不可能供我們姐弟3人都讀 大學,我很清楚作為一個女孩的卑微。
我要讀書,就得自己掙學費!可那個年代,青壯年都難得多掙一分錢啊!
我當時想到的掙錢方法有3個。
一是搬著竹竿去打樹上的蟬蛻。蟬蛻是一味中藥。可是分量太輕,價格也低廉。我攢了兩竹籃 蟬蛻,才賣了5角3分錢(人民幣,下同)。
二是爬樹折柳。小販收購的是那種把皮剝得乾乾淨淨的曬乾了的細細長長的柳條,用來編花籃。八分錢一斤的柳條,比蟬蛻壓秤多了。於是,我像男孩子那樣去爬樹,樹上的毛毛蟲真多,把我身上的每一寸皮膚都咬出大大小小紅疙瘩。剝皮、曬乾,好不容易賣了7塊8角錢,收柳條的小販卻突然不來了。於是,我轉而割草。
我們那裡是棉產區,春夏秋,牛吃青草。冬天,牛吃乾草。會持家的婦女,總是在夏天多割些青草,曬乾了扭成草把,齊齊地碼在廊簷下,留著冬天餵牛。而那些沒儲備乾草的人家,冬天就只能買別家的乾草了。乾草3分錢1斤,不愁銷路。我於是開始了瘋狂割草的日子。
每天大清早,我就拖著板車上路了。我熟悉村子裡的每一寸土地,知道哪裡的草藤子長,好扭草把,也知道牛最愛吃哪一種草。早晨天氣涼爽,我會跑到遠一點的地方。一邊割草,一邊把草曬在田埂上,這樣中午拖回去時,就會輕些。
避開中午毒辣的日頭,一般在下午3時左右,我又會拖著板車出發。這時候,我會選近一點的地方,為了讓幹活晚歸的母親,幫我把草拖回去。
割草最深刻的記憶,就是熱和渴。汗水有多麼鹹澀,我是用眼睛嘗到的。眼睛被汗水浸泡,又黏又辣睜不開,因為雙手是泥,我只能低著頭在衣服上蹭。滿臉滿身都是泥漬,我是一個真正的灰姑娘。
更難受的是渴。帶去的瓶裝井水,很快就見了底。喉嚨裡幹得冒煙的時候,我也捧過溝子裡的水喝。但只是潤潤唇,不敢吞下去。那水裡有農藥啊!
那時候的天空,一定比現在明澈。可是,再乾淨的天空也不能解渴,再白胖的雲朵也不能餵牛啊。又乾又渴的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吃上一根冰棍。
田間小路上經常有騎著自行車賣冰棍的人,5分錢一根的冰棍,於我卻是不可企及的天堂。我身無分文。賣蟬蛻和柳條的錢,都被層層地包裹在奶奶的手帕裡。那是我讀書的錢,是改變我命運的錢啊!
我一面幻想著那賣冰棍的人是我的舅伯,一面在心裡暗暗發誓,等我讀好了書,我要馱一箱子冰棍回來,專門發給那些割草的小姑娘吃。
那個夏天,我們村方圓五里的草都被我割完了。師範錄取通知書是在一個傍晚傳到我們村裡的。當時我正在鏟村醫務室門前的草。赤腳醫生義安姨舉著一張紙片朝我喊:“容娃,快把鏟子丟了吧!你的手,以後要拿粉筆了!”
鏟子鐺地一聲掉在地上。我笑得稀哩嘩啦的,接了那張紙片就往家裡跑。板車是母親後來去拖回來的,鏟子沒有找到。母親第一次沒有為丟東西罵我,反而說:“丟了好丟了好,以後,再不要你鏟草了!”
那年冬天,我家的乾草除了餵自家的牛外,還賣了38塊5角錢。那時候讀一年高中的所有花費也就30、40元。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考上師範,我會在下一個暑假,再重複一遍這樣的匍匐。
生活沒有如果。生活以它不可抗拒的力量推著我向前。師範畢業後,我先在鄉鎮教初中,然後調到縣城教高中,逐漸成為學校的把關老師。如今年過半百,但我做人做事的心氣未減,勤勞節儉的品性未改。我從不罵黨罵社會。因為,我是農民的女兒。歷史上沒有哪個朝代農民的女兒能像我這樣,風不吹,日不曬,一雙手被粉筆灰滋養得雪白。
我同時也感激那個給了我饑餓與苦難的地方。那個地圖不經過的地方。天門。嶽口。耙市。豐嶺。那個地方,曾用最母性的草汁,餵養了我家的黃牯牛,餵養了我的青澀年華,也餵養了我不屈的靈魂。
我性格中的自卑與倔強,都源於那裡。15歲那年夏天,我匍匐在地上的身影,是我一生的姿態。我願意一輩子流著自己的汗水,收割自己的夢想。我願意一輩子舉著這支筆,舉著這光陰的燈盞,不讓命運暗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