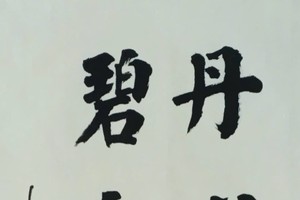立刻歡天喜地地收拾房子。打掃乾淨後,給已經泛黃的石灰牆貼上兩幅喜愛的畫,書桌上擺上教案和自己喜歡的書,再插上一束花,簡樸得跟瓦房極為相襯。坐在籐椅上,舒服地把頭靠在椅背上,一縷金光從屋瓦的空隙間射了下來,原來是這瓦有些漏了。
九月,在南方還是盛夏的季節。從酷熱的水泥樓房的教室走進我這清涼的瓦房,實在是愜意無比。同事都極喜歡到我的房中小坐,戲說我這裏是“避暑山莊”。不久,“避暑山莊”又改名號了,叫“觀雨軒”。這雅號得益於我那房頂的破瓦。
記憶中,夏季的雨應是驟來驟去的,可那年卻下了個不亦樂乎,整整下了一個星期。小雨轉中雨,中雨轉大雨,大雨成暴雨,太陽像趕場一樣,只偶爾露個臉,匆匆地來,匆匆地去。唱主角的,還是這似乎下不完的雨。我的房間可就頗為壯觀了--白雨跳珠亂入“房”。雨頑皮地從屋頂鑽下,爭先恐後地溜下來,窗外是巨大的雨簾,房內則是一條又一條雨綴成的白練,有的粗些,有的細些,落在地板上,淌成了一幅又一幅寫意畫。我把房裏所有可盛水的盆盆罐罐都用上了,因“白練”太多,盆子罐子放的位置也就據漏大漏小而各就各位,各司其職。乍看像佈下了“迷魂陣”。看,“大珠小珠落玉盤”;聽,大珠滴落如“大弦嘈嘈”。小珠滴落如“小弦切切”,真是“嘈嘈切切錯雜彈”啊!
同事皆笑:五星級享受啊!我也笑,說道:“李義山曾講留得殘荷聽雨聲,我呢,是‘幸有屋漏觀雨景’。”
這雨景並不在雨天才有,雨停了,房間還有一段時間淅瀝淅瀝的呢!水痕依舊,地上的寫意畫天天變化無窮,任其哪一位畫師,恐怕都不能須臾變化出這麼多的畫面來,的確是創意無限。那殘留的雨水從瓦縫中漏進來,滴在硬紙板鋪就的天花板上,水積成了一灘,濡濕了硬紙板,那水,慢悠悠地從上面滲下來,落到接水的罐子裏,許久一滴,打破屋子的寧靜。雨休“漏”卻不盡,實在是別有一番風味。
忽一日,校長告訴我漏瓦已換了。我很惋惜地歎道:“那我豈不是不能屋內觀屋雨了?”
“放心吧!你的觀雨軒還會重新開張的。“他又說:”屋瓦太舊了,又有野貓上房扒屋瓦,你這兒遲早還會漏雨的。要不要考慮換一間休息室?”
我謝了校長的好意。我喜歡看雨如斷線或如圓珠地淌下地板;我喜歡聽雨叮咚或滴答地打在罐底。
不知不覺間,我調離這間學校又快10年了,對當年作為休息室的那間瓦房,我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依戀和割捨不了的情結。我是在留戀那一場場承載記憶和幻想的雨還是留戀那一去不復返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