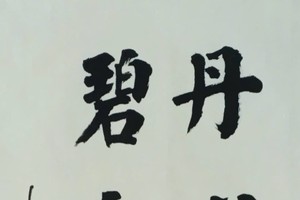(一)
事情發生在半個世紀前,那是1960 年的夏天,在艱苦中努力攻讀了6年之後,我和好友孫小龍終於考完了高中畢業試,同時準備從海防到河內上大學。
為了放鬆一下長年累月因學習而緊崩著的身心,也應小孫的四叔──勛叔的再三邀請,我們決定到和平省山區的支那鄉村去旅遊。
支那,是和平省偏遠的一個少數民族的村寨,離河東市鎮50公里,聽小孫的叔叔孫勛說,支那原是個人煙稀少的小村,後來從南方北上集結的部隊在那裡駐軍,從泰國回來的一批越僑也在那裡落戶,加上有條從河東到支那的公路,每天有返往兩班客車,使這個原本寂寞的山區村落,也開始有了熱鬧的氣氛。
出發那天,我們從凌晨4點就坐上海防到河內的火車,又乘河內到河東的叮叮噹噹的有軌老電車,等到河東車站時,已是晌午時分,從河東開往支那的第二班客車已開走。正當因錯過而茫然之際,忽然開來了一輛小貨車,小貨車的司機願意載客,但說只走至河東到支那的半路。在走投無路之下,我和小孫只好硬著頭皮上了這輛小貨車。
經過上貨卸貨和兩次的拋錨,顛顛簸簸的小貨車,終於開到了一個小村落,司機叫我們下車,並指著前路說,從這裡到支那還有30公里要走。然後卸下貨,往回開車揚塵而去。
暮色蒼茫,天已晚了,周圍一片漆黑。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我和小孫一臉的茫然,不知所措,兩人舉目向前眺望,見黑暗中,前面有幾點亮光,我們預測,那有人家,便舉步向前走去。到了那裡,經一打聽,才知道這裡是個十來戶人家的小村落,但大都已關門閉戶。這時刻,正好是饑腸漉漉,我們便走進一戶還開著門的人家。這是一家鄉間的小吃店,經營著狗肉和米粉的生意,由於天晚了,狗肉已售完。但透過燈光,我們看到廚桌上還擺著一個已煮熟的狗頭,狗頭張開嘴巴,露出兩排白色的牙齒,彷彿在向人們申訴著牠的冤枉和不幸。看了這情景,我們心裡涼了半截,但迫於無奈,因為太餓了,我們只好在店裡吃了米粉和蝦醬,又匆匆赴路了。
夜,漆黑一片,前路茫茫,怎麼走呢?還有30公里的路程。思來想去,小孫告訴我,不如到一戶人家租舖睡一晚,等天亮再趕路,這樣穩當又安全。我同意了。
黑暗中,尋來覓去,折騰了一個時辰,我們才從犬吠聲中找到了一戶人家,打算住宿一晚。
我們向老屋主出示了學生證,並交了租金,老屋主安排我們住在他的中間屋,屋裡有一張大睡床,大床睡3個人,我們倆和老屋主,屋主睡在最裡面,靠近神檯的地方。
我們開始入睡。夜深深,周圍除了蟲鳴聲和偶爾一兩聲犬吠之外,再沒有其他的聲響。
睡著睡著,忽然一陣咳嗽聲驚醒了我們,原來是老屋主在咳嗽,咳了一陣之後,他下了床,拿起地下的痰盂,不斷的吐著痰;又睡了一會,老屋主又咳嗽,咳嗽之後,又是不斷的吐痰。見情況不妙,小孫拉著我的手悄悄說:“天呀!老人患的是肺癆病,我看見他吐的是血!”聽後,我心寒而慄。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們向老屋主委婉告別,說著要赴路,於是走出了家門。
鄉村的夜,漆黑,陌生,四處蟲鳴,偶爾有一兩隻螢火蟲飛過,還傳來一兩聲貓頭鷹淒切的啼鳴。
鄉村的夜,前路還有30公里路要走!
30公里的路,我們迎著無邊漫漫的黑暗。
30公里的路,我們聽不完的蟲鳴和野獸的怪聲。
30公里的路,我們聞不盡路兩旁的濃郁的野花香。
30公里的路,我們憑著一隻手電筒,一根竹棍,兩雙腿,尤其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意志!
30公里的路啊,我們從子夜12時,一直走到早上6時,才看到遙處人影憧憬,那是當地少數民族同胞到梯田勞作的身影;同時也聽到陣陣歌聲,那是部隊駐軍凌晨的廣播聲響,這時刻,我們才長長的舒了一口氣,到了勛叔所在的軍墾農場◆ (待續)